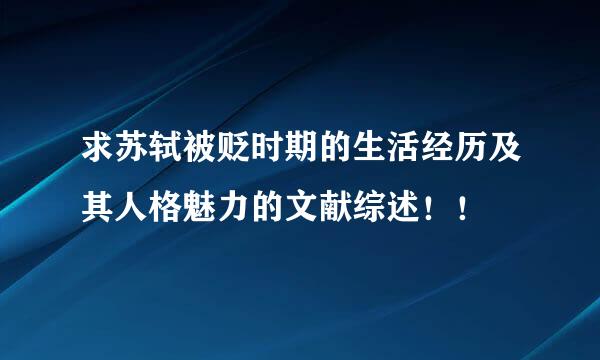
苏轼的橘肢哪仕途经历是坎坷的。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饥绝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因先后不容于改革派和守旧派,苏轼在仕途上两起两落,被贬达十余年之久,几次因诗文获罪,“乌台诗案”差点使他丢了性命。然而,在沉浮不定的人生面前,他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力,横遭贬谪也好,自请外放也好,都没有使他颓唐丧志,不管身居何处,无论爵位高低,他都能随遇而安,有所作为。他尽管屡遭挫折却能够始终保持一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金山题像》一诗,是苏轼赴常州时写下的,可说是他对自己一生作的一个最好的总结:“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试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东坡的人格魅力是永恒的。 林雨堂在他写的《苏东坡传》中这样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我们可以说,他是诗人、画家,是散文家、书法家,是乐天派,是道德家,是百姓的好朋友……可是这些都还不足以描绘他的全貌,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天才所具有的深厚和广博,苏圆码东坡像一阵清风一样度过了一生,虽饱经忧患,却始终不失其赤子之心。” “苏东坡的独一无二,还在于他的平民气质。一个经常被放逐的官员却有着最多的人缘,文人骚客、贤士大夫自不必多说,难得的是他与野老村夫、渔樵僧道,都能找到沟通的话题。一千多年来,有那么多人热爱他,是因为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魅力。苏轼的魅力是一个谜,在他身上包含了最大限度的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传统文化通过他这个载体历久弥新地在当代社会呈放光彩。” 构成苏轼人格精神主流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这种思想,塑造了苏轼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仕途顺利时,他身上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精神十分突出。而被贬后,便是为百姓办了一件又一件好事:在徐州,他亲自带领官员防洪、筑堤;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在广东惠州,他引泉入城,供百姓饮用。此外,各地的东坡井、东坡书院,惠州的东坡孤儿院,海南的东坡医疗所……也都是苏轼为民创下的实绩。苏轼的人格魅力,显得格外鲜明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