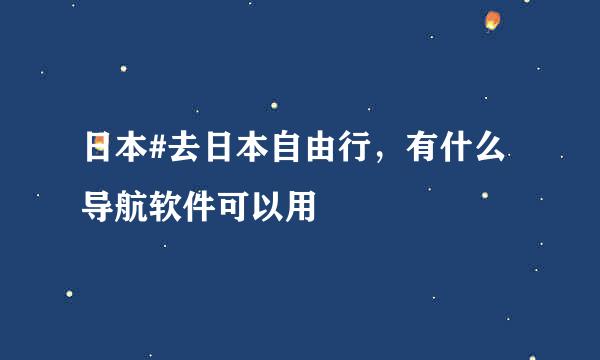序 胡汉民[1879-1936,原纳尘名衍鸿,字展堂,广东番禺人。国民党元老之一。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12年1月民国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长。后来曾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主席(1927年4月)和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1929年3月)。 英国的历史家韦尔斯【韦尔斯:英国著名作家,毕业于英国皇家学院。其著作有《时间机器》、《隐身人》、《世界简史》等。】,于今年春间,发表一篇文字,同情于中国革命,而警告欧洲人,内里说及欧人之了解中国,决不如中国人之了解欧洲,大意欧洲人只是一些教士商人以及替教士商人说话的几个新闻通讯员,他们耳目既然狭隘,而带了着色的眼镜观察,更其靠不住,至于中国人呢?却是一年一年许多留学生到欧洲,受学校的教育,和社会接近,经过长期的体察,自然不是前者之比。这一种比较的批评,认为公允,几乎令欧洲人不容易反唇相讥,中国人也觉得非常悦耳。不过我们一搜查中国留欧学生关于批评欧洲有系统的研究较为成器的著作,好像还未出世,中国人对于韦尔斯的公道评论,就怕要暗暗叫声惭愧。 不要说欧洲,就是日本,我们又如何呢?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一半相同的,风俗习惯是相去不远的,留日学生较之留欧学生,数量要多十几倍,而对于日本,也一样的没有什么人能做有价值的批评的书。从好的方面说,小心谨慎,不轻于下笔,也是有的。从不好的方面说,就无异表示我们学界科学性和批判力的缺乏。季陶先生说,我十几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一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的装置起来。现在《日本论》一书,就是季陶十几年来做他所志愿的工作写出来的结晶。我前十年听见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两个日本同志说,戴先生作长篇演说的时候,他的日本话,要比我们还说得好。我拿这句话来赞《日本论》,我敢说,季陶批评日本人要比日本人自己批评还要好,是否武断,且让读者下最后的批判。而我所以敢说这句话,就因为他不止能说明日本的一切现象,而且能剖解到日本所以构成一切的动力因素,譬如一个武士道,在日本是最普遍的伦理,好像英国的gentleman,日本人自己李腊也弄到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季陶先生说:武士道这一种主张,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山鹿素行(1622~1685)日本江户前期的儒者、军事学家。曾从著名的朱子学者林罗山学习儒学,后又研习军事、神道、和歌学、佛法等。宽文年间,他对被确立为官学的朱子学的抽象性展开批判,主张儒学的实践性和日本的学问体系,提倡古学,因此获罪流放。晚年获准回到江户。主要著作有《兵法神武准备集》、《武教全书》、《山鹿语录》、《中朝事实》等。】、大道寺友山那些讲武士道内容的书,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的扩大和变迁,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明治维新,都知道是起初打着尊王攘夷的招牌,而幕府一倒,后来政治的建设成绩,却大过当初的预想。这是天皇圣明吗?是元勋元老的努力吗?是统一的效果吗?直到明治四十一年,日本文明协会丛书出版的《欧美人之日本观》,还是说,我们动辄把日本维新的成效归功于日本人一般的天才,事实却是相反,日本之一大飞跃,只是指导者策划得宜,地球上任何邦国,没有像日本指导员和民众两者间智力教育、思想、伎俩悬隔之大的,而能使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无何等嫉视,不缺乏同情,就是指导者策划设施一切得宜,他们遂能成就此之当世任何大政治家毫无逊色的哪茄滑大事业,(略见原书中篇第一节)这样浅薄皮相的话,我从前看见,就觉得肉麻得没趣。而季陶先生说:那时代欧美的民权思想,已经渐渐输入进来,汉学思想和欧美思想相融和,就有许多人觉得这一种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这实在是由种种环境发生出来的“自觉运动”。……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这民权运动是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和萨长两藩专靠强力来占据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权运动最有力的领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国卢骚《民约论》的感化,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却是唤起日本人的同胞观念,使日本人能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而我们更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材料来证明“辩证唯物论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合革命史上全部事实。[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是戴季陶主义的主要观点,]譬如日本维新的结果,解放了农民阶级,使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这个运动并不是起自农民自动,而仍旧是武士阶级当中许多仁人志士鼓吹起来的。 季陶先生在日本维新一个大过程中,并不是抹煞一切指导者的劳绩,不过他有很深的理解,和上述《欧美人之日本观》的一段肤浅可笑的议论不同。他说: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的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作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彼人的信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所以普通人看日本维新史,都晓得萨摩长门并起,而长藩的人物,一直延续到今日,尚成为日本的军阀,萨藩的领袖西乡隆盛,却是失败的英雄,只有追悼他维新以前的勋业。而季陶先生说: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败者的福。我们试把这几十年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当时随着他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公论的推移,定他的改策。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征韩论:由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于幕府末期、明治初期提出的侵略朝鲜的论调。明治初年,木户孝允等主张把戊辰战争时动员的军队用于征韩,后由于日本与朝鲜的邦交谈判陷入僵局,征韩论得以通过。但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后来又主张解决内治,于是西乡下野。这次事件也成为自由民权运动和士族叛乱的开端。】,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是闯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人格也都埋没干净。 这一段话,抵得过别人一百篇西乡的传赞。我们只看西乡当王政统一的时代,举兵造反,犯了弥天的叛逆罪名以死,而死后不到几年,他的铜像巍峨矗立于上野公园,受全国人民的崇拜,并且全日本没有一个铜像可以和他并称的。至于伊藤博文【伊藤博文(1841~1909)政治家,分别于1885~1888年、1892~1896年、1900~1901年四次担任首相。1871年任岩仓出访团副使访问欧美。1873年升任参议兼工部卿。1882年主持拟定宪法。1885年任日本首届内阁总理大臣。1909年10月赴中国哈尔滨与沙俄协商侵朝事宜,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枪杀。】事业上的成功,从表面看来,中外人都觉得他远过于西乡,死在高丽人之手,也是殁于王事,而他的铜像,在东京被人打倒,甚至搬到大阪,也不能成立。这些事说明了什么?就是说明毕竟成功的是失败了的西乡,而不是伊藤一辈人,长藩的领袖虽然享着福荫,毕竟是有限的。季陶先生这一段话,我想任何日本人都不能反对,不过见不到,说不出这样彻底罢了。 我常以为批评一国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一民族特性难。政治有许多明显的迹象,就是它因果联络关系,也容易探求而得其比较。至于一个民族的本真,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社会,如季陶先生所说的,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还要切实钻到它社会里面去,用过体察的工夫。韦尔斯说,欧洲人不知中国,其重要意义就在此点。我们看了上中下三篇整千页的《欧美人之日本观》,觉得他无甚心得,并不深刻真挚,也是此理。到得本国人说本国的民族,这些条件工具是比之外国容易完备了,然而却有第二种的障碍,这种障碍更是不容易打破,其由外力支配所生的障碍,姑且撇开,而自身的因缘成为心理的拘囚偏执,就会弄到如黑智儿(即黑格尔——编者注。该书注解均由编者所加,后不赘述。)那样一个大哲学家,抬起德意志民族,认做神的表现,世界的选民,其实如季陶先生此书所引吉田松荫《坐狱日录》一段话,也和黑智儿的出发点相同,不过一个穿了古代神教的衣,一个穿了近代哲学的衣而已。《大学》说得好,“人莫知其子之恶,而莫知其苗之硕。”上句是由于爱,下句是由于贪,真是不把种种“之其所……而辟焉”的障碍打销,决寻不出鞭辟入里公平至当的批判。批评自己的民族,犹之批评自己本身。近来有见识的人也晓得说说,如果真是一个革命者,就能对自己作公开的批评,这话是不错的。自己的检查,比别人的检查更为便当。责备自己,应该比别人的责备更为深刻。然而事实上往往不然。遇着老于世故人情的人,反而善于用责备自己的口头话来作辩护自己的手段。浅之如张作霖骂张学良,说这小子太不懂事,深之如莫斯科CP本部,骂中国CPCY幼稚,都是假责备来为自己辩护的。日本人批评日本,说到自己短处,晓得回护不来的,也每每犯这种毛病。然而因为他有他的立场,我们应该原谅他的。白香山的诗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该诗题目应为《题西林壁》,为苏轼所作。)批评自己的民族,仿佛有这个道理。而“我田引水”,又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季陶先生说:一个关闭的岛国,他的思想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特殊的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 他们以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岛,居然能够滋生发展,平定土番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支配许多土著和外来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们更从高丽、中国、印度输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够通通消化起来,适应于自己的生活。选出一种特性,完成他的国家组织,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民族的数量现在居然可以和德法相比,在东方各民族中,取得一个先进的地位,这些都是证明他的优点。我们看见日本人许多小气的地方,觉得总脱不了岛国的狭隘性。看见他们许多贪得无厌崇拜欧美而鄙弃中国的种种言行,又觉得他们总没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们在客观的地位,细细研究他,实在日本这一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算是十分可敬。总理说: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要以自信力作基础。这的确是非常要紧。所以日本人那一种的“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 大抵批评一种历史民族,不在乎说他的好坏,而只要还他一个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季陶先生这本书,完全从此种态度出发,所以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同时又做了他的审判官,而且是极公平正直不受贿托,不为势力所左右压迫的律师审判官。说日本是信神的民族,不含一些鄙视的心事。说日本是好美的民族,也并没有过分的恭维。一个自杀情死的事实,说明他是信仰真实性的表现。这一种科学的批评的精神,是我们应该都提倡的。 季陶先生这次回到上海,一见面就说:“我近来又做了一部日本论,可惜今天没有带稿子来给你看。”我说:“此之前几年登在建设杂志的那篇《日本论》怎么样?”他说:“你先说你对于我的旧作,有什么意见。”我说,那一篇文字好是好的,不过我觉得主观过重,好像有心说人家坏话,人家有些好处,也说成坏处了。他说:“对得很,简直被你一言道破,我这回改作的一部日本论,却完全是平心静气的研究,决没有从前偏执成见的毛病,我明天带来,你看过觉得不错,就请你作一篇序。”到第二天,他果然把稿子带来,一眼望去已经是十多万字,他笑着说:“我做《建设》和《星期评论》文章的时候,我总是将稿子带来寻你,站在你的椅子后面,把捉着你的手,按到纸上,而我却一句一句的朗诵起来,遇有商榷的疑问,才始停止,商榷过了,又是继续的朗诵,我认为是我生平一件快事。现在这部《日本论》太长,可惜用不着这个顽意。”我和他都不觉大笑起来,及他去后我费一日一夜的工夫,将他这本书细细读过,真有点爱不释手的光景。看过从前那篇《日本观》,尤其觉得这书有味,不只他的研究和构成方法,和旧作不同,就是文章也有异样的色彩。季陶的文章,大概有三个时期不同。第一个时期是从做《天铎报》,以至《民国杂志》,雄畅是他的本色,惟有时修词的工夫,有些来不及。到《星期评论》、《建设杂志》是第二个时期,既改文体为话体,大畅所欲言,而修理整然,渣滓绝少,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了。现在这部《日本论》,就更加陶练,深入显出,不露一些辛苦的痕迹,理解的精确,而文章的能事,足与相副。其中如《今天的田中大将》一个题目下,指摘世界的思潮。《信仰的真实性》里面,发抒他的人生观,都是博大雄深的文字。而《秋山真之》一篇,仿佛极善写生的短篇小说。《好美的国民》一篇,却含有许多诗意。在做《国民杂志》那时候季陶先生常对我说,自恨做文章的工具不足,现在应该没有这种遗憾了。其余还有许多绪论名言,往往可以摘取出来,或作国民一般的殷鉴,或作青年行动的指针。而季陶先生却是偶然证合,有感斯发,既不是“我田引水”“削足适履”,也不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垒块”,季陶先生的高声朗诵,确是“奇文共欣赏”的方法。我在一日一夜之中,欣赏所得,就随手写些出来当作一篇序文,贡献于阅者,并留着许多说不尽的好处,让读者自己去欣赏。固然介绍这部日本论,应该还有重要的意义,不止是从这本学得科学批评的方法,和鉴识季陶先生最近的作风。但是中国人何以有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季陶先生开宗明义,已经说得清楚尽致,不用我来赘述,这并不是我的忽略,我想青年一经提醒,决没有做智识上的义和团的。 民国十七年